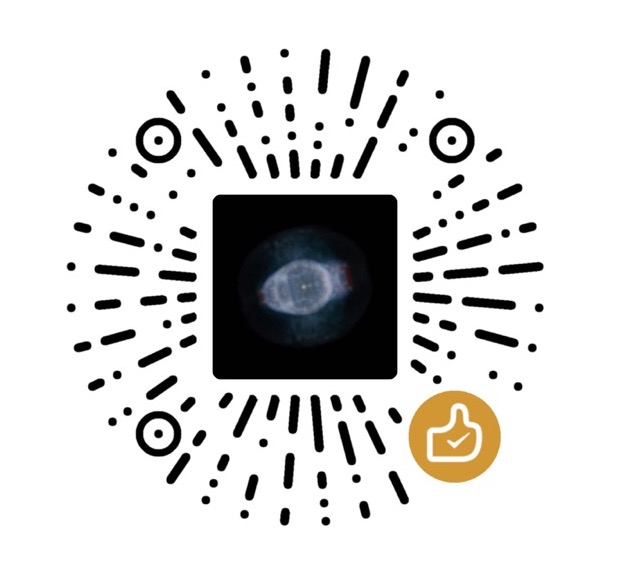「据说,那鬼笔先生是世家之后,家风犹存,写得一手好字,奈何家境清寒,便在襄阳城里,搬了一张书案,日日以卖字为生。大多数时,给那些三教九流不识得字的人写写家书,也有的时候为那么些个大户人家抄抄书。话说,有一日,鬼笔先生替一位唤阮娘的小娘子送家书给岳阳的父母,路过一处坟茔,谁知,那坟墓一个雷劈下来,竟然裂出一道黑黝黝的缝隙来,缝隙里伸出一只骷髅手,手上就横握着那支笔,骷髅屈不起手指,反倒像是要举着那支笔托到空中去。」
「那时,阴风怒号,狂风大作,这荒山野岭,竟是要下起一场泼天大雨来。鬼笔先生看着点点鬼火聚在那坟墓旁边,像是捂着什么似的发亮。他一点也不害怕,接过了那支笔,只匆匆忙忙下了山避雨去。等到回程,他又路过了那处荒山,只见青天白日,哪有什么墓……」
这里是洛阳城外的一处长亭,来来往往的过客在这里歇脚,便有说书人和卖凉茶卖酒的聚在这里,使得旅人能够歇歇脚喂喂马。在长亭的角落里,一个清瘦的灰衣年轻人放下自己的书匮,要了一碗茶水,付了一点钱,避开阳光坐在褪了黑漆的栏杆上。
听得说书人说着这些真真假假、添油加醋的传闻,只是无奈地笑笑,捧着一只豁了口的黑陶碗,用双唇吹开一碗的涟漪。热气消散在空气里。不一会儿,一个湛青衣裳的带刀武人进了这处长亭。年轻人扬了扬秀气的眉,目光垂下,仍旧去饮茶。
那湛青武人穿着皂靴,暗纹圆领袍子,两侧开衩,露出里面的松绿袴,腰上束着蹀躞带,插着一柄小银刀,并一把鱼皮鞘的长刀。蓝色幞头下的面容仍旧是沉冷的。他一进来,环顾了一圈,便走到那个年轻人身边坐下。
另一边仍旧是热火朝天。
「你们知道,现在江湖上悬红最高的三样东西么?」
「现在,江湖上悬红最高的三样东西,不巧,主人都是同一个人。悬红最高的,是鬼笔先生的笔,」他竖起一根手指,身躯微微倾着,脸上也带了一丝狂热,「一万两黄金!」
「其次,八千两黄金,」他比了一个八字,「悬的是鬼笔先生的头!」
「最次,五千两黄金,」他朝四下笑了笑,「悬的是鬼笔先生写字的那只手!」
「鬼笔先生笔不离手,手不离身,身不离头,只要找到鬼笔先生,那就是两万三千两黄金啊!」众人皆啧啧赞叹。
「嘿!——不知道这等好事可能落到我头上!——若是我见到那鬼笔先生……想来也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,我就……」
「诶,话可不要说得太满。」说书人微微压低了声音,「这鬼笔先生,身上还带了案子——前几日,据说是范太守的外室死了,范太守接到了一张纸,上面也不知写了什么,竟让范太守发了疯病,大理寺追了下来,正在到处寻鬼笔先生的踪迹呢!」
「可是那益阳太守范同温?」
「正是!」
「啊,我倒一直听说,那范同温是远近闻名的孝子,彩衣娱亲的事不知做了多少。」
只这一句,诸人并不说话。
年轻人皱了皱眉,喝干了一碗苦茶。他背起书匮,正要走出来,那湛清武人起身,按住了他的肩膀,在他耳边轻轻道,「郗鉴。找个地方说话。」
「大理寺陆司直,你跟了我一路。」
出了长亭,两人到了后面的山坡上。风过,竹林发出沙沙声响。
郗鉴翻了个白眼,自顾自把双手伸过去,「算了,我打不过你,你绑我去大理寺吧。」
陆轻焰不语,「我验过了,阮娘是自杀的,我已经去信给阮娘的家里人了,唯一的问题是范太守。」
郗鉴似是无奈,「你去信给她家里人有什么用,她家里人早不要她了,还要给她出丧葬费,哪里肯。」
「范太守是如何疯的?」
「我不知道。」
「颖阳张生案、新郑卢生案、鄢陵王公子、扶沟陈吏……还要我再报么?」
「不……不必了。」
郗鉴眸光转了转,「这范太守么,我不大熟,他有一日来找我,是为了向我求一篇文。」
「什么文?」
「谒荆王书。」
这回陆轻焰沉默了一下。
「你知道的,我的笔好,一般人看了我的文,是难以拒绝的。倘若是小娘子让我写一篇情书,浪子也立刻回心转意;倘若是公子让我写一篇和诗,花魁也会对他另眼相待;倘若是小人让我写一篇谒文,再中正的清流都会觉得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」
郗鉴笑了笑,那笑从竹林清风之中透过来,爽朗肆意,「我的文可是很贵的。你想看吗?不过,如果是你,我可以送你一篇啊!」
郗鉴放下了书匮,从里面拿出了一卷纸,从笔匣里拿出了一只笔。陆轻焰的目光情不自禁地投向了那只笔,乍一看那只是一支挺平常的笔,以湘妃竹为骨,貂毛和翠羽为笔毛。翠羽的蓝光从黑墨之中透过来,陆轻焰一时移不开目光。等到再凝神一瞧,那湘妃竹的泪斑在日光下隐隐流动,透出了陆轻焰熟悉的,血的光芒。
郗鉴只寥寥写了几笔,便用书刀裁下,笑眯眯地盯着陆轻焰的表情。
陆轻焰接过那张泛黄的麻纸,凝目,心口一痛。天旋地转的世界像是被拔出了池底的塞子一样,漩涡一样吞进他的视角。等到再抬起头,额角已是一层细密的冷汗。
郗鉴仍旧是笑。
陆轻焰摇了摇头,「郗姑娘。」他对郗鉴这恶劣玩笑,仍旧是宽容的。他的声音微微沙哑,「你还是快走吧。——去忘机阁。」
郗鉴不可置信地看了他一眼,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」她吹了一声口哨,缓缓走上了洛阳城的古道。
十五日后。仍旧是那个长亭。益阳事毕,陆轻焰早已等在那里。古道尽头黄尘漫天,上百骑锦衣呼应着当中紫衣的一骑,绝尘而来。
颜凛空下了马,径直朝挎刀的陆轻焰而来。
「我听说范同温被流放了?」
「是。」
那天陆轻焰带着大理寺的人冲进了范府,久病的范老夫人吓得当场去了,在她床下,竟发现了整整四大箱的金银财宝。谁都不知道这件事的起因,仅仅是一个妓女的自杀。
——她叫阮娘。她和妹妹幼时逃荒被父母卖了,三年前妹妹不堪忍受,郁郁而亡。阮娘在风月场中的脂粉钱都省下来贴给父母,欢场中,本就活得艰难。谁想到呢,这个范同温,连妓女的钱都贪。加上阮娘的父母一直催信来,让阮娘给弟弟娶亲贴钱。阮娘把毕生积蓄给了范同温,头脑一热一冷过后,终于意识到了这辈子赎身无望,父母又催逼得紧,一个想不开,在一个森冷的夜,将那条夹缬披帛,抛上了房梁。
郗鉴多次替阮娘读写家书,不由起了悲悯。欲报复范同温,就用那只鬼笔,让他日日陷于噩梦之中。
「我曾经听说,欧阳平的入室弟子中,有一个姓郗的,大约就是这个郗鉴了罢。」颜凛空慢吞吞地道。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,「我在路上,还听了另一个故事。」
范同温家里是落魄旁支,八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,靠母亲当街编草鞋为生。后来范同温登科及第,官运日上,终于做了一方太守。或许是年少时的清苦,在成名之后加倍而来。年少时失去什么,便会不断贪求,紧紧握在手里。他母亲这辈子没有什么爱好,吃的都是糠食粗蔬,穿的也都是荆钗布裙,范同温也是一样,吃穿用度都极为简朴,丝衣都没有两件。范母这辈子没有什么享福的乐趣,就是喜欢把金银珠宝压在枕下床下。
「那倒是个孝子。」陆轻焰不带感情道,「可惜,他要在八千里外守孝了。」
颜凛空不语。他目光落下,看见了陆轻焰苍白的脸。
「你怎么脸色这么不好,可是发生了什么?」
陆轻焰摆了摆手,「没事,做了几个噩梦。」
「走吧,回去吧。折冲府也巡完了。」
「颜凛空!」陆轻焰忽地唤他,「如果你是范同温,你会怎么做?」
颜凛空回头看她,那双黑黑的眸子反而沉了一口气,他拂了拂衣摆,「君子固穷,不如守中。」
陆轻焰摇了摇头,低声道,「可惜没人会问阮娘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