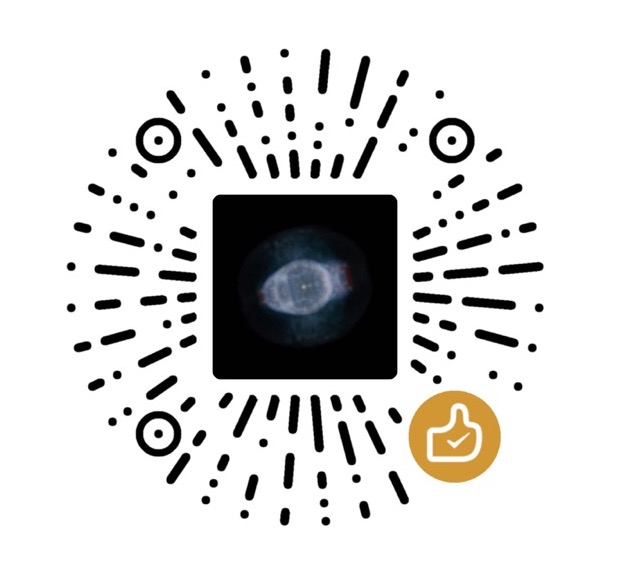第一次见宛怡的时候……我也忘了是什么时候。林林总总,七七八八的事情太多了。青春芜杂而斑驳,在荒野里蛮横生长,躁动,好奇,渴望……揭下无限可能的面具,实则不过是围猎之前,对猎物最后可有可无的温存。
未见之时,听到宛怡的大名比较多。她在高中时就是校刊主编,发过许多不错的文章。参加某知名作文大赛,众望所归得回了一座大奖,随即是顺理成章的保送。她是从小便披着「才女」的羽毛衣裳长到大的,这衣裳越裁越长,盖过脚面,拖过了身后,像孔雀华丽丽的大尾巴,一袭浓墨般的夜色,闪着孤光、寒峭深沉的浓绿。
第一次见她的时候,首先来的,是一些纤丽的瘦,像宋瓷一样。随后就是衬着刘海的一双眸子,有种幼鹿呦呦的感觉,是一双易碎的眼睛。倘使路上遇到了教人伤心的事,是抿一抿就能下泪的眸子。也是一双在影院昏暗角落,皱皱眉就能泛着涟漪溢出来的眸子。
这匆匆一面,就像落在睫毛上的一闪。
第二面的时候,导师让我去给 A 教授送些材料。走过香樟成荫的林荫道,进了凉匝匝的门厅。我来到 A 教授的办公室门前,抱着资料,换了一只手,腾出右手来敲门。
过了一会儿,门里传来一声厚重的「进来。」
我说明了来意,A 教授似乎不是很高兴,冷着脸让我把材料放在桌子上。我尴尬地出去,不好意思地朝坐在沙发上的宛怡望了望。宛怡陷在黑色的沙发里,膝头摊开一本皮面的活页笔记本,两手交错,指甲陷在肌肤里,捏红了,低着头,握着钢笔的手在微微抖。
我走了出去,忘了带门。
迩后,不知怎地,宛怡文字上的才华便暗淡下去了。但宛怡受 A 教授喜欢倒是很多人都知道,宛怡经常被叫去整理资料、誊录分数。我只知道宛怡看上去越来越不合群,形单影只。也有些风言风语,但我觉得这只是叫那些人嫉羡的残羹冷炙罢了,不以为意,继续不务正业地翘课、约会、打游戏。后来宛怡考了 A 教授的研究生,我读完本科之后,便随大流涌入人潮般的市场,约会,加班,年终奖。
过了三年,我已经从菜鸟混成了一只老鸟,在项目里带带新人。一天,收到了一个好友邀请,正好奇间,仍旧下意识点了「添加」。
是宛怡,她辗转拿到了我的微信,约我出来。
我来的晚,她一个人坐在角落里,肩胛骨微微含起来,似乎要把那瘦弱伶仃的身子骨藏到藏无可藏的尽处去。
她似乎是习惯于沉默了,只是一直捧着咖啡杯的厚厚杯壁,听着我说话,时不时地迟疑点点头。终于,我也觉得讲无可讲,沉默着靠在沙发椅背上,拈起杯盘,心不在焉地啜饮一口渐凉的咖啡。
「最近常常回想过去的一些事情,写下来……突然就想到了你。」
「坠入悬崖之前,一些微小的星星之光,总也要致谢一二。……我人生的后半生,一直在泥淖之中挣扎窒息,却也总是不敢轻弃,觉得对不起父母……」
我从久远里隐隐摸索出了什么,却不敢承认,只能问她,「你将来有什么打算。」
她摇了摇头,「不知道。」
我只是叹了一口气。
……
后来么……后来,陪伴她的春草一枯一荣,萋萋了三载。陨灭和希望一样,都是可以自我生长的。少有人同情她的自杀,没有人想得到她会在一个连绵雨夜,将一根细细的皮带置在了自己颔下。我知道宛怡,她并不需要同情,或许她只是追着她纯粹的那个世界去了,而把身外的一切、周遭的我们,单独剩在了荒腐的此岸作为惩罚。她的葬礼很安静,A 教授亦出席了。这葬礼安静得可以在沉默中杀人,仿佛余生都这样窒息了下去。
我不知为什么,在当初匆匆见她一面时,就隐隐觉得那是个易碎的女孩儿。美丽一直是个易碎的东西。但我宁愿它坚韧一些。后来我或许明白了,坚韧是于美丽有伤的品格。
我无法劝她放开一些。杀死她的是 A 教授,是不堪的回忆,还是割裂的自己?我不是宛怡,我不知道。她无法与那些事情、那些自己达到和解。人们纷纷议论她的死亡,觉得是文学和她的孤高害死了她。我只知道大多数人只会要求她带着溃烂的伤口,含恨、屈辱地活下去,这是宽慰者挂在口边礼貌的本能。他们不知道,他们所颂扬的坚强或许本身就是杀死人的品格。
女儿开口学会叫「妈妈」之后,我紧紧抱着她,最初的激奋人心的欣喜散去,我竟然对着女儿的无邪面容开始叹息发愁,直欲深深下泪,为着她来到这个世上而怀以歉意。这决定慎而重之,却还是带了错误。她生的太美太好。我看着她的眼睛,意识到她那双幼鹿呦呦的眼睛,那双轻易地为饥馁为一切不顺遂嚎啕大哭肆意暴雨的眼睛,才惊觉,我和许许多多无能为力的人一样,或许是理解的,但却是冷漠而纵容的。这种冷漠和纵容在见过宛怡的那一双如宋瓷冰纹般碎了的眼睛之后,就时时在心头叩问。我以为我忘记了,其实它一直如影随形,追着我,使我无端写下这些话来。
窗外,起风了。卷起一阵一阵的香樟枝叶。我向来觉得种香樟是很惫惰的,一年四季常绿,少有「四时之景异也」的意味。如今,在大多数树木萌叶之时,它来一场荼蘼而荒废的落叶谢幕,风里、雨里,都是香樟叶子的味道。以前我用迟钝来回避,和好友吹风时说,香樟应该叫「低调的引诱」。这种人不该遇见。虽然不会惹得一身花香,但它用一种理性诱导,它的叶子,它的花,它的木质。于是城市就受了它的诱导,到处都种香樟,哪里都是香樟。但树毕竟比人可爱,它的诱导仅仅是抢了几个窗户的阳光,而人的诱导,不止抢了几个人生的轻灵无邪。
雨淅淅沥沥。这风,这雨,这落下的香樟叶子,渐渐织成了罗网,紧紧扼着沉默的喉咙,使它无法嘶唳呐喊。它每一句都在最深的尽头呐喊,而太多人希望它闭嘴。
雨夜渐渐销沉了下去,不知道多少人的声梦将涸。
题图摄影:**Photo via Visual hunt** 图片授权:CC0协议